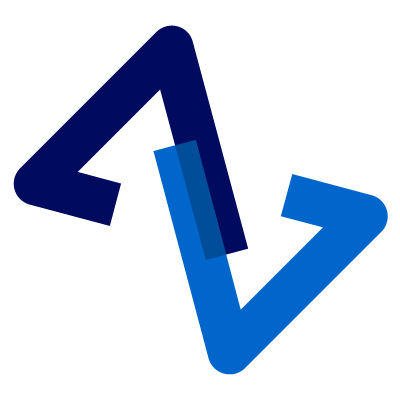俞翔元醫師公益講座
時間:109年3月21日 下午2點至5點(全長3小時)(上)
講題:當我對你說謊時,是它在說真話
主持人(邱三姑):
我代表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歡迎兩岸三地諸位老師、各位夥伴,今天來參與我們這一場專題講座。這一場專題講座,是我們為了慶祝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的成立而辦的。原本是一場地面的課程、地面的專題講座。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改為網路,也因此得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陸的諸位老師們結緣,也請大家多多指教。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初出成立,還有諸多需要完備的地方,也請大家多多支持和指導。我們今天的講題,是由我們協會理事長俞翔元俞醫師來幫我們主講。俞醫師是我們第一屆的理事長。他是一個詩人,就我所認識,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詩作挺多的,然後是一位文人、精神分析家,還有插畫師。他也出版了兩本自己從頭到尾是他畫的一個插畫的書本。這一次非常難得,因為我們能夠以一個結合符號學、語言學、精神分析,特別是拉岡理論下的精神分析來做一個講題。我想這是一個外溢、跨界的一個主題。因為俞醫師本人浸淫在這個領域也有相當長時間。所以我想等一下他的演講一定是如行雲流水。俞醫師目前是在台南,跟我是同鄉,是開業的、執業的精神科醫師,那麼也做精神分析,所以他領導我們協會在未來是朝比較靜態的翻譯一些比較經典的著作,還有動態的,就是做一些校園講座推廣。還有辦一些象徵性收費的公益課程。那我就不多耽誤大家時間,現在我就把時間交給俞醫師。
主講人俞翔元醫師:
謝謝三姑的介紹,我這邊很感謝今天榮幸能夠在這邊為我們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舉行這次公開的講座,原本這場講座是預計在台北的地面舉行的。那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改到線上來。也因此,我們在線上能夠有機會,可以跟更多的人相處。那我想其實像廣場恐懼者,常常會抱怨說他們去偌大的空間,他們會感到畏懼、會感到害怕,那其實他們看似是在害怕距離,其實他們一方面是在呼喊著距離,因為他們太靠近無法分離的焦慮。那我想也許我們平常太近了,我們在這個線上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反而我們用聲音、或者用影像,反而能夠更接近彼此,能夠有機會,能夠跟我想我們這邊的不管是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的會員也好,或是任何對拉岡派精神分析有興趣的這些同好也好,或是對岸的我想已經算是先進或前輩們也好。我們今天能夠有幸在這邊跟大家聚在一起,今天的演講,我想好像除了我之外還有一些台灣精神醫學的先驅,包括靜和醫院的陳宜均陳醫師,那我這邊也先跟她問一聲好。
那麼我今天要講的講題,大家一看的話也許會有一些不了解,我這邊的講題是《當我對你說謊時,是它在說真話》。
首先的話,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我的很模糊的文件,大家可能覺得說,為什麼不用一般的Power Point就好了?那我想這個也是增加一下大家對這堂課解讀的一個難度。為什麼要增加這個難度呢?我想,拉岡都說我們不要理解得太快,精神分析就是一個不要理解得太快,有時候要懸置我們的理解的一個記憶的一個工程,一個多情的一個規訓。那我想為什麼,我們總是好像太快的去在想像界中去解讀我們分析者的一些意象也好,或者是說幫他們做出很多的規劃也好,那我想這個拉岡的《文集》本身,這個《文集》的法文來說就是一種書寫,一種描畫以及一種描摩,那我想也許用這種方式,一種回到比較人工的這個書寫的方式,那我們也可以回到拉岡的這個思想的本源。他說書寫是不可解讀的,那文字是可解讀的,那我們這邊結合這個圖畫跟文字的方式,讓我們來達到一種這個也許是無意識的本源的真相的部分。
那我們現來講這個當我對你說謊時,是他在講真話。那我們可以看到直接我跟你,似乎這個就是一個面對面的,可以是在當下進行交流時的相互主體性,但這時候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就是始終有一個他在說話,那這個「它」,這個「它我」,台灣這邊也許過去都會翻成「本我」,那我們這邊回歸本源,這邊講的是它我,佛洛伊德的行文是非常簡潔的,它包括我、自我跟它我,這個它我,是他在講真話。
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右邊大家看到這個說謊者的悖論,所有克里特島民都說謊,那這句話到底是謊言還是真相?或者是羅素講的,有一個理髮師他替所有人,跟不為自己剃髮的理髮師剃髮,那他到底要不要為自己剃髮呢?這就會陷入一種悖論,這種悖論就是說,當說話者的內容牽涉到說話者自身的時候,這個就會形成一個短路,一個無盡的廻圈,我們會不知道他到底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這看似跟我們精神分析沒有甚麼關係,但我們回歸過來的話,我們可以連結到我們的臨床經驗,很多的分析者來到我們的分析室,一開始都會有一些很明確的請求,比如說請你解決我的痛苦、我的困擾,也許是跟伴侶之間的摩擦衝突,也許是他沒有辦法出門,因為他害怕交通工具,沒辦法搭飛機,沒辦法去到廣場,也許是他有一些強迫性的洗手的症狀,總之,很多他沒有提出的一些要求,那如果我們只是在這個要求上去回應他們,根據他們說話的內容,他們的要求去給予他們一些建議,不管是情感支持也好,或者是給他們一些這個工作性的聯盟以及依循目標之一也好,你們就會發覺很快的就會陷入一種廻圈,一種無效的打轉。
這是甚麼意思呢?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有一個受暴的這個分析者跟你說,他可能常常跟他的伴侶陷入一種相互傷害、折磨或是甚至是肉體虐待的關係,那也許他這一次這麼說,下一次的時候又跟你說,其實我們倆個又復合了,我們又很恩愛,我想他一切都會改變;再下一次的時候他又跟你說,其實我已經有認識新的人,那過去的這個戀情我已經要告別了;再下一次他的話語、他的欲望又改變了,我們始終無法確定他講述的內容它的真假,常常到最後的時候,可能這個分析者說,其實我並不知道你要什麼,我跟你之前講的話,可能所有都是謊話,因為我自己也騙過我自己。所以,這個自己的話語跟自己的發話這個本身的一個矛盾,那當然羅素的話,是提出了他的邏輯的階層論,去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們就是說拉岡的話,他的特別之處的話,他是直接的用彷彿亞歷山大大帝一樣,用利器、利劍去斬斷這個高迪安之結,他直接把無意識跟意識劃分開來,或者說我們說闡述的立場跟講述的內容,就是大陸那邊可能說「陳述」跟「述陳」,台灣這邊可能是說是「說」跟「話」,說的主體跟話的主體之間的分裂,或者說可以延伸到欲望跟要求之間的分裂。那高迪安之結的由來就是說,傳說那個能夠解決這個高迪安之結,解開這個高迪安之結的人,是一個無比智慧的人,就可以統治歐亞大陸。很多年來都沒有人可以解開這個結,那亞歷山大帝到那個地方的時候,他一反之前所有人可能用傳統的方式去解這個結的方式,他直接就揮一把刀,把這個結給斬開,那這個結就斷裂了,那當然這個跟後來他的豐功偉業是有關係的。那我想拉岡在這邊就是很明確的提出了這個無意識跟意識,然後說話的講述跟我們這個陳述的內容之間的一個分裂,那剛剛的例子就是這個樣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就是我們精神科的這個教科書常常會提到的,比如說有一個分析者跟他的分析家,陷入了這個很相互糾葛的愛欲的轉移,那可能常常會這個跨越一些界限,那最後這個分析家就不得不離開這個工作的機構,這個故事可能在我以前工作的醫院或是說診所也好很常發生這種事情,就是沒有辦法處理好這種想像的這種攻擊侵凌的關係。那往往這可能這個分析家離開了這個機構,這個分析者,前分析者,還是會一再的反覆回到這個前分析家工作的地方,那也許去哭訴呀、也許去怨尤,去抱怨說他如何被遺棄、被丟下。那這個有一次他就被收住院了,那收住院之後,那個主治醫生就問他說:「已經那麼多年過去了,為什麼你就不能再投入一個新的分析關係,或是說再跟新的分析家,重新新的分析呢?」那這個分析者就說:「我只愛他不行嗎?」那這個教科書裡面的一般客體關係派的這個分析家就說:如果你早愛他,你早應該為他而改變了,所以你的愛不是真實的愛。那我們會說這個分析家其實回應的是很貼切,也許他看到這個愛的背後可能是恨,或是說克萊恩會說沒有辦法把這個愛跟恨這個部份客體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客體。當如果我們回到這個分析者,他自己講的話來看的話,我只愛他不行,這時候也許我們拉岡派的去專注在他講的言說的語句上面,我們就可以直接去給他打一個標點了,到底是愛他是「不」?還是,是「不行」?是「不」?還是「行」?他自己就有一種否定或雙重否定了。或者是我們另外一種滑脫好了,我們說我只愛他不行,就是一種我阻礙他不行,阻礙是甚麼?他的只愛其實背後是一種阻礙,如果說是一種近似音的話,他阻礙自己去愛嗎?還是他阻礙著他自己,他阻礙著那個分析家嗎?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只是單單的一句話,他其實就已經蘊含了他自己無意識的欲望的真相,我們右邊的這個L圖就可以看到了,也許他跟那個分析家的關係,是處在這個a跟a’ 的小他者之間的想像關係,但是他自己所說的話,會從大他者那邊,自動重覆性的回覆他自己言說的一個真相,他並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但他所說的內容,比他自己原本所意向的說的更多。那我想對岸那邊,也許大家都是這個拉岡派的一個實踐多年的這個很有經驗的前輩,那台灣這邊的話,因為剛起步,所以我們還是先回到最原初,我們先從拉岡派最特別的就是包括語言學以及能指這個部分開始說起。
那我儘量把這個部分,從最基本的開始延伸到比較中後段比較進階的部分,讓這個比較入門者,跟比較有深度的這個已經鑽研多年的人都有一些收穫,這個難易度之間可以都顧及。那我們先回到最初這個最基本的部分,我們說我們精神分析最重要的就是傾聽,那傾聽的最基本的單位是甚麼?這邊就直接說了,回到最基本的單位,傾聽最基本的單位就是「能指」,這個能指也許大家剛入門的時候,其實就會遇到一些難關,什麼是能指?什麼是所指?那對岸那邊翻譯可能是「能指」跟「所指」,台灣這邊台大沈志中教授把它翻譯成「意符」跟「意旨」,那交大的劉紀蕙教授跟南藝大龔卓軍教授翻成表記跟所表項,這是在《拉岡精神分析詞彙》裏面的,那我想這都是同樣的,只是各有各的側重的部分,那如果就沈老師的這個來看的話,可以直接看到意符,它就是一個一種符號,一種指號,它是乘載著最低不可化約單位的意義的一個符號,所以我們說它是一個意義的最微小的單元,是我們傾聽最小的單元。
那不管是意符也好,能指也好,拉岡這個都是從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這邊來開始、借鏡開始發展的。那索緒爾本身在生前並沒有出版過任何的書籍,但是他過世之後,由他的學生幫他整理出版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最有名的就是作能指跟所指的一個區分,能指就是所謂的音響的形象,而所指就是概念的形象,這樣子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區分。當然我們這邊不要被誤導了,音響形象跟概念形象的形象,並不是我們所謂心理的那種形象,那只是指的是意義的最基本的單位,當然索緒爾是在研究印歐語系的各個語言之中,把它還原出一個語言系統裡面,最公共、共有的普遍的一個法則,索緒爾除了分開了能指跟所指之外,他還區分了比如說語言跟言語,那我想這個大家也是必須要熟稔的部分。我們來說語言並不是指的是比如說法語、德語或者是中文這一類的,漢語這種一種特別的單一的語言,語言它指的是可能是一個所有語言所共有的一個普遍的一些法則的基礎的共通語言;而言語呢?我們可以是說英文的speech跟language的差別,言語的話或是言說,指的就是說每個主體在其獨特的各自的一個發明或是重新的運用跟創造,這兩個一個極端的,就是這兩個不同的對比的話,這個也是進入拉岡的精神分析很重要的一個必須要先理解的地方。
那拉岡還取材這個除了能指跟所指的區分,還有語言跟言語的區分之外,另外一個側重的就是任意性的部分。我們說比如說就這個原本的這個索緒爾自己的舉例好了,我們舉中文的樹木,漢語的樹木好了,我們講到樹木,大家會想到甚麼呢?聽到樹這個音的時候,語詞的時候,也許大家眼前就會浮現了一座可能是枝葉茂密,然後樹幹很蓊鬱,然後樹幹堅挺,然後樹根很扎實的一顆樹,在我們的心理的意象裡面,那為什麼樹,這個樹是叫做樹呢?根據這個語音的不同呢,這個樹,比如說為什麼不是數?淑?書?或是促?這個每個音都會有個滑動,都會指稱不同的詞語。那索緒爾就說,這個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任意性,為什麼樹叫做樹?這個就是一個,最低限度的一個武斷,一個任意性的部分。所以,這個是一種約定俗成,沒有一種自然的一種規約性。那之所以使用這個索緒爾的這個結構語言學的這個能指跟所指,這剛好是我們必須要去,我們目標是要研究主體,研究這個分析中,分析者的一個言說,那我們去歸結到最低的這個單位,就是能指跟所指的區分。
那另外,拉岡還受到這個諾曼.雅各布遜,後來的布拉格學派的這個結構音位學之分的一個影響, 那音位學,我想大陸那邊的人,可能叫做音素,音素,就是說我們仔細的去分析一個語句,然後語句裡面切分,可以分成句段,然後音節、音段,那最後的話,可能最基礎的單位就是音素。那我們知道印歐語系是非常講究這個語音中心的,他們是一個表音的文字。那至於漢語的話呢,漢語我們基本上,這個能指的最低的單位,我們會說可能是詞語,像我們剛說的樹木的部分,但是漢語的特殊性的話,是它的漢字本身,就是這個象形的圖像性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影響的影響力,因此一直以來語言學上,漢語呢到底是一個詞本位?還是一個字本位?這個一直都有所在爭執,但我們回歸來說的話,如果說能指的話,我們可以說它大多的時候指的是一個詞語,詞語就像我們剛剛說的樹的部分。那諾曼.雅各布遜除了說這個音位、這個音素的這個研究之外,另外影響很大,就是我們後來會提到包括編碼跟訊息之分,這個我們在講述大他者跟大他者訊息這個部分,還有這個症狀、語誤跟遺忘的部分,這個都會有所連結。那雅各布遜還有這個所謂兩種失語症的劃分,包括無法使用隱喻跟無法使用換喻這個部分,這個也深深的影響了拉岡。
那第三個影響,就是列維.史特勞斯,台灣翻譯成李維史陀,他的結構人類學。列維.史特勞斯是研究這個美洲那邊的很多的原住民,後來發現說,其實亂倫禁忌,如此的影響著人類,但是,他並不是根源於優生學。我們最直接,我們就舉個可能是物競天擇,可能是優生學的考量,所以才有亂倫禁忌,我們禁止族內通婚,當他去研究時候發現,這是因為一個象徵效力,一個符號的作用,我們超越了個體的意志,去決定了這個包括不管是親屬關係的一個基本的結構,血親、或者親人,或者說姻親,以及女性交換這些,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象徵的效力所決定的。所以,這個另外他在這個研究人類學裡面,使用了很多結構主義的一些數學的方法,比如說神話素,或者一些很多圖表式的使用,那另外還有包括研究一些靈位的符徵,那包括像是嗎哪,或者是壕,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符號象徵,這些也深深地影響了拉岡。
另外還有一個影響很大的是,拉岡的朋友本維尼斯特,本維尼斯特在一篇經典的論文中有提到陳述跟述陳的分別,或者是講述歷程跟我們的陳述內容「說」跟「話」的一個分裂。我們在這邊仔細的講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本維尼斯特區分的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點,在一個特定的情境,在某個具體的發話者,他講述的那個我,跟他那時候講述內容中的那個述句中主語的我,兩種是不一樣的、是分開的。就像現在講話的我跟我講話內容裡面提到的我,這個是分裂的,這個部分也是影響著拉岡思維很重要的部分。
当我們前面进行鋪墊講完之後,我們來看這個能指的一個、幾個,我整理的幾個公理,應該不是叫公理,應該叫命題。第一個:能指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唯物論,為什麼是唯物論呢?拉岡很清楚的說道,能指是一種唯物的科學,它並不是所謂的感性或理性的直觀,也不是一種意象,甚至不是我們所謂心理的原型,雖然我們在傾聽,或是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專注的是一種很唯物的一個素材,不會是去傾聽一些飄忽的情感、感覺或是說我們的一些想像的交流,或者說像是一些意象的練習之類,我們就直接專注在這個能指上面,而能指在多數的時候拉岡指的是詞語,少數,也有的時候指的是字母,當然說這個是遷涉到很多很深层次的、后面很多身心醫學的研究,尤其是現在比較火熱的,這個字母比較跟這個所謂一些生理症狀跟區體化相關的,這個比較接近實在一部分,我們在這裡就先不講。接著所以我們注意那個詞語,就是在這個裡面的音素、形素。那當然拉岡在分析–維拉斯奎茲的《宮娥》圖–一个繪畫的時候,他把那個繪畫也叫做能指。所以有時候這個能指似乎是很多符號的化成言語、語言的一種或是共通性的說法。那我們這邊提到不可分割性,我们就很會想到一个哲學的原初,就是德謨克利圖斯提出物質的最小的單位:原子,原子是不可分割的,那當然我們知道到後來原子可以再細分成:質子、中子、電子或者甚至夸克,把這個更細分,但是這個精神就是我們分割到最後一定有個不可分割的單位。亞理斯多得說過實體害怕真空,但是就量子力學來說,物質到一定的單位之下,它正面看去是物質,但可能旁視側觀來看的話,它卻是一片真空,所以我們說意符或是能指也是,它似乎是承載著一定的意義,但是我們旁視側看來說,它就又是一種義意的缺席。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缺席的意義或一種無意義跟些微意義、跨步意義的一種辯證,這邊法文是Absence de sens跟non-sens、peu de sens 、 par de sens 似乎它在自己之中有閃爍的意義的一點微光,但很容易又熄滅了,如果用比較細的來看。為什麼會這樣子呢?能指的義意是如何的建立起來?後續會慢慢的提到說它必須跟其它能指的結合或是撞擊之中閃耀出意義的光輝。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繼續看下一個命題來說,我們會說能指它並不是一般的記號、訊號或者我們說的一般的這個圖標也好或者這個所謂的圖畫也好,他並不是一般的記號或者編碼,能指並沒有固定、單一、普遍的意涵。比如說我們就舉例來說,動物或是昆蟲有沒有符號呢?其實是有的。我們如果說有稍微一點點這個動物行為學或者是一點生物學的基礎,我們都知道蜜蜂其實也會傳遞一些符號的訊息,我們可能說那是一種符碼一種code一種固定的單一圖片的意涵,比如說蜜蜂牠發現了某個地方有食物的來源,牠就會飛回原本的蜂巢去,然後跟其他的蜜蜂跳了牠的一個搖擺舞,那搖擺舞就會傳遞給其他蜜蜂一個訊息說,這個可能在跟太陽夾角一定的角度下多遠的距離,有食物的來源。這時候其他的蜜蜂就會知道,在多少的距離之外有這個食物來源。然後他們也可以去那個食物的來源尋找,其實動物之間也有這樣的符號的一個傳遞。
但是能指跟這所謂的這些符號是不一樣的,在這個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皮爾士的符號觀,就是右邊這個區塊。皮爾士的符號,其實大家唸的符號學大部分剛開始看都會看到皮爾士的符號學(大陸是翻皮爾士還是皮爾斯)似乎好像所謂的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地位又慢慢被這個皮爾士取代了,我們再看一下說為什麼,皮爾士的符號學跟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不一樣,結構語言學就分成能指跟所指,皮爾士的符號學是一個三叉體,它是一個三元觀,他把這個符號分成表現體,表現體(representamen)表現體本身是符號的意思,以及對象和解釋項,比簡單的來說的話,表現體本身就是符號。她依從著我們要指稱的對象,譬如說我們要指稱那顆樹,然後去傳達產生某一個解釋的意義,這也跟剛剛的語言學以主體為出發的觀點不一樣,符號觀他是從個體符號觀來出發的,比如說,他很明確地說到,這個對象客體–我們要指涉對象的客體是主動的,而我們的符號是被動,而那個對象是一個自變項,那這個符號表現體是個依變項,那所以我們要依循我們的對象去產生符號,那至於解釋項就是所謂意義的話又是第三性的,就是根據我們的符號本身再去依變。那我們來看他的依據對象的符號很基本的分成三個,初階是象似符,第二階是指示符,第三階是象徵符,那這就是從低階到中階到高階,象似符像是所謂的圖表、圖示、圖畫,甚至在最高級的象似符是所謂的想像。
第二階的指示符是根據時空的鄰接性或是根據特徵來進行,譬如說交通號誌是一種象似符,禁止前進打叉叉的符號就是個象似符,有動物會跑出的這個動物跑出就是一個象似符,至於指示符比如說外科醫師在開刀的時候在這個肚子上面畫一個印記,在手術的時候根據那個肚子表面的印記去畫開,然後開始去找那個盲腸炎的盲腸,這時候時空的一個蹤跡的毗鄰性的話,這個就是指示符。比如說煙跟火的關係,產生的煙之後我們都知道可能有火,這一種指示符的關係。
至於更高階也就是所謂的象徵符,象徵著是一個社會的約定形成的一個公有的一個符號,我們在這邊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符號的世界中,每個主體一出生就活在符號的世界中,就算是自然物也是可以成為符號。我舉例石頭,也許最早時石頭也只是石頭而已,這時先民發現舊石器時代或是新石器時代,石頭經過敲打及磨製,石頭就可以變成一個工具,變成石斧、棒棍之類的,這個時候石頭就變成一個有使用價值的。但人類除此之外还会有符號的意義的,譬如說我去到一个地方,去到花蓮的七星潭好了,發現七星潭邊這個海邊七星潭也叫作坦途海,它那邊有很多很漂亮被浪花淘洗着變成很圓潤的鵝卵石,那我選一顆一帶回家,那回家后我每次看到這顆石頭都有想起那一次旅遊的記憶,那种美好的不管是海浪聲或者是在那边可能一些很惬意的往事,那么这个時這個石頭就帶有我個人的符號的義意。这个时候我把這個石頭送給朋友(三姑)做為一次旅行的紀念品,這時就又帶有交換的義意跟價值在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也许会把这个石頭會打造成玉珮,那这个玉珮就又帶有象徵的意義,如國家玉璽、王位傳承及皇上身份的標誌,他在每一个詔書上蓋上玉璽的印章代表著通行法令等,但是這个是需要可以流變的,像藺相如完璧歸趙去找秦王時,那個玉珮就變成了一個工具,那時藺相如拿起玉佩說若是秦王不依的話,我就要一头撞上去把玉珮粉碎,這時玉珮就變成一個使用工具、一個武器。任何的東西進到人類都會自然帶有符號性的意義在裡面。
那我們說皮爾士的符號觀因為依據這個對象客體,它可以解釋幾乎所有的符號的表意的過程,所以它使用的範圍非常的大,甚至動物也好或非言說的主體也好,但是他會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說,每一個符號都是像一個三叉體一樣,它是有根、枝、葉,那像是一個三叉,我們也許拿著符號的木棒去碰觸對象的一個木頭產生意義的火花,但是這三個叉本身又可以再演繹下去,就比如說這個對象本身又可以再接續著其他的符號,所以說這個三個叉都可以進行無限的演繹或分叉演繹,所以這個是一個幾何倍數式的一個分裂的一個表意過程,所以其實這個會馬上陷入一個迷霧陣一樣,我会说這可能原本是那個樹枝、樹根式的一個符號表意,這會變成類似像德勒茲的一個分裂書寫根狀形式的散漫書寫的方式,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精神分裂式的,沒有一個錨定點的一個分散書寫。另一個極端就是所謂符碼性的,如果我們要規避一個結果,每一個符號都只有一個單一固定的意思,變得像我剛講的蜜蜂的一個傳遞特定的訊息一樣,那我們也許這就是從一個單一重複的就像妄想症似的這種單一重複。好我們先不講這個了。
我們現在來講,能指並非記號或指號,我們這邊講的是拉岡第一個公式,符號的話是為主體代表某人、某事或某物,但是很明確地精神分析的主體是什麼?精神分析的主體是一個能指的主體,這句很重要!精神分析的主體是有一個能指為另外一個能指來代表,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能指的主體是要為另外一個能指來代表,這個差別在哪邊呢?我們來舉個例子,就像魯賓遜的例子,《魯賓遜漂流記》,一個人在那個荒島、孤島上面過的很孤寂,所以他一直想要有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來跟他同伴,有一天他就在海灘上發現了有人的足跡,他馬上欣喜若狂,這個島嶼上也許有其他人可以來跟我做伴,但是他又很害怕這個足跡到底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所以他很仔細地必須把自己走過的足跡都擦拭掉,之後他必須非常小心的,他不要留下自己的足跡以去區辨其他人的足跡,我們說這個就是一種一個能指為另外一個能指,去塗消掉自己的能指,來為另外一個能指來表徵自己的主體,所以能指並不是孤立的,他必須要連接到另外一個能指上。另外一個例子我舉的是阿里巴巴的例子,大家應該看過童話故事《天方夜譚》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這個阿里巴巴有一天進入到這個山洞裡面,看到這個盜賊把金銀財寶藏在裡面,要進那個山洞的方式就是喊「芝麻開門」就可以進去了,所以他之後就知道喊芝麻開門就把金銀財寶都帶回家了,當然我們知道後來這個盜賊頭目想方設法就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家,于是又去他家門上面做了一個記號說,之後就要來把這個家放火燒了來洗劫這一件事,然後這時候阿里巴巴很聰明的婢女瑪姬把所有城內每一戶人家的門上都標上記號,所以我們會說,原本那個盜賊在阿里巴巴家門上標的那個記號,當所以城上的門上都被標上記號的時候,我們就說這是能指的系統,大家可以領略這樣的差別。因此我們會說拉岡所謂的能指的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主體內或者主體間性的,而是我們能指間性的。主體本身是沒有辦法自己自生,而是由一個能指來為另外一個能指來代表,那另外的能指之所以它不是像計畫一樣的一個單一圖片的意涵,他是因為我們所有能指都是相互對立、差異跟分解的、是一個相交比較的,所以我們分節articular這個字跟構音是一樣articulation。
我們舉個例子,中文也很常有這樣的說法。你家離我家近不近啊,然後可能我不會說近,我們會說不遠。這時候近跟不遠是一樣的。那我們一開始舉的個案,那個愛的對立面不是恨,愛的對立面是冷漠,那時候愛的定義就由冷漠來定義了,那冷漠的對立面是愛嗎?似乎又不是,那冷漠的對立面可能是激情,那激情的對面是什麼,是欲望嗎?無欲嗎?那我們說在一系列這樣的意義就在各種對立分歧中相互挪移在對照。底下我們講的陰陽、雌雄、乾坤,這些都是由相互對立差異之間去展佈去羅列的,那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能指的系統裡面,數字1跟0跟 -1是同樣地位的,有跟無跟沒有是一樣地位的(即:1 = 0 = -1)。如果我們要去切進陰性或女性在象徵的位置,拉岡中後期會說非全邏輯(没有一个),我們中後段會再提到。
我再舉個例子,比如說「和平」的定義是甚麼呢?我們可能會說「和平」就是所有的國家都對其他國家友好,這是「和平」的定義。但是另一個說法我們可以說,「和平」就是指沒有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發動爭戰。這個時候「所有」的全稱可以用「沒有」來說,那我們會說也許和平就是有一些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去協調各個單一國家的事務,是有一些特稱的,有一個例外在,而這個例外的話我們又可以說成是「並非沒有一個」超越了國家單位的國際組織在。所以這個特徵「至少有一個」,我們就可以說成「並非沒有一個」。所以拉岡說這個所謂的通過者,就是通過制度的這個分析者,這個Par sans,就是一個並非沒有、並非不知道的主體。這個扯遠了,我們先講到這邊。
那第三個公理的話,就是能指對所指的優先性。我們底下看到這個圖畫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在索緒爾原本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裡面講到,能指和所指就像一個圓盤一樣可以正反翻面的,一面是能指,另一面就是所指;一面是音響形象,另外一面就是概念形象。所以因此當我們講到一棵樹的時候,他的背面可能就是畫著一個樹的形象的樹,但是拉岡把這個完全顛倒過來,把它變成右邊這個圖形,一道橫槓,上面是樹的文字,下面是一棵樹,也就是說他把能指放在所指之上,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相互顛倒的原本的意義了。而那個橫槓是去阻離,或是去壓抑底下的所指的。因此這就是拉岡所說精神分析就是不要理解太快。我們所指,或是我們所謂的涵義,都永遠不是立即可以獲得的。我們可以說理解在先的就是一般的閒談或空言,理解在後的可能才是精神分析的真言。我們剛剛說「樹」的時候,並不一定意味著直接我們剛剛想到的腦海中的那棵樹。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我們用羅蘭.巴特的例子來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羅蘭.巴特的《神話學》,它裡面跟拉岡的觀點不一樣,但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很有趣的這個所謂「涵義內容掏空的現象」。我們先看左邊這個,馬蹄鐵(horseshoe)這個表達的能指時,右邊的所指是右邊畫著的這個馬蹄鐵,這個是很簡單的,我們說一個馬蹄鐵,我們指的是具體的馬蹄鐵。語言的特色是甚麼呢?這個能指和所指,我們又可以把它當成新的能指來看,所以在西洋的語言裡面,當我們提到馬蹄鐵這個能指的時候,它又帶著所謂「幸運」的涵義–這個所指。所以原本第一階的表達跟內容,在第二階變成了表達,那第二階又有新的這個內容,所謂的幸運的、象徵的、約定俗成的一个涵義。那到第三階的話,當我們提到,比如說在電視上面看到馬蹄鐵的時候,這時候馬蹄鐵已經超越了原本的馬蹄鐵的單一的涵義了,就是說它指的可能是原本的那個馬蹄鐵,當然也有可能指的是幸運的意思。因此羅蘭.巴特把這個第一階和第二階說成是語言,第三階說成是神話。這是他的分析,他還用此來分析很多時裝、運動、音樂或是流行的現象。
這邊大家可能還是不是很理解,我這邊右邊來舉一個另外的例子,這是我自己舉的。當我們提到「黑旗子」這個能指的時候,我們所指想的是這是一個黑色的旗子,這是第一階,那第二階我們說到黑旗子的時候,除了包括這個黑旗子之外,我們可能聯想到黑旗子是安那其(anarchy),「無政府主義」的一個代表。所以因此可能在詩歌的裡面,第三階講到黑旗子的時候,詩句裡面說到出現黑旗子的時候,他就不只是一個黑旗子了,他就帶有神話色彩的火光在裡面。比方如說一句詩句裡講到說「我們沿著漫長的國際線逃亡,黑旗子一直伴隨著我們。」這時候的黑旗子可能就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可能跟流亡,可能跟永恆的反抗者連繫在一起,它都帶有神話色彩在裡面。因此就連一個單一的能指,比如說不管是馬蹄鐵也好,或者是黑旗子也好,它就已經蘊含了原本的所指的對象,另外還有象徵的意涵,那這個就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單獨可以直接去獲得的固定的一個意義了。
那當然這跟精神分析裡指的「能指優先於所指」不太一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拉岡的,我這邊底下舉的一個例子是傅柯(大陸譯作:福柯)的例子:這個畫是一個馬格利特的畫,他畫了一支煙斗,然後在上面用法語寫著「這不是一支煙斗」,那這個就造成一種荒謬、錯謬、錯亂的一種幽默感,因為我們看這明明是一支煙斗,但他卻在上面寫著說「這不是煙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傅柯根據這幅畫,寫了一本小冊子,很有智慧的小冊子,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說明這不是一支煙斗。這個很明確我們可以有很多種解讀。我们可以说,本來這個圖像、這個象似符它本身就不是跟真實對象的煙斗對象是相同的,那另外文字,底下寫的這個煙斗的文字,這個能指它本身也不是真實的煙斗啊!甚至這個像似、這個圖像,跟指示符,它本身也是不一樣。所以單單這個一句話跟一個煙斗的畫,就已經引進了多重分裂、無法鈕結跟所謂保持一種意義的錨定性。那右邊是馬格利特的另外一幅畫,他畫了一個小黑板,黑板上面也一樣畫了一支煙斗,上面寫「這不是一支煙斗」,又畫了一個空中的一支煙斗,如果喜歡解讀的聽眾可以再去解讀,這裡面有多重的表徵再現和以及其中的這個斷裂。
那拉岡會說「能指優先於所指」,所以「所指」在「能指」下面不停地滑動。他畫了這個圖,就是A跟B,這個像波浪一樣的圖,他說這個圖「像在創世紀上手抄版的插圖出現上下兩層水的波紋,使這雙層的流體間,以垂直的虛線繪成的細線彷彿像雨絲那般纖細,用於界定兩兩相對應的部分。」能指和所指兩個上下不停地滑移,中間聯繫了他們穿越的意義就像是雨絲一般。他舉的另外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個,橫槓上面是指男性和女性的意思,那上面各畫一道門。這個故事是說:在火車行駛靠站的時候有一對姊弟,弟弟看到說我們快要到女廁了耶,姊姊就跟他說:笨蛋,我們到的是男廁!所以就是說他們由不同的座位、不同的角度,他們到的時間,我們看到同一扇門,這個門明明長的是一模一樣的,卻是因為上面的男性或是女性的字、或字母或是上面的標誌,我們就把一模一樣的這個門解讀成男性和女性的廁所。這幅圖可以說是拉岡對索緒爾或是對弗洛依德的一個戲仿。佛洛伊德說「解剖學即命運」,似乎是生殖器官決定了男女的性別。但是在性差異的議題上似乎能指或是所謂的象徵的效力似乎是起了更大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兩扇門長一模一樣,但是它「意義的沉澱」卻乃至於上面分別寫上男性和女性,用的廁所的差別,它就形成律令,就形成說我們滿足自己生理需求的時候我們要進入不同的隔間,如果進入錯的隔間我們就會被社會風俗譴責。
第四個公理,能指它有一種在場性。能指在場卻是以不在其位的,也就是說以其缺位的一種在場性。這邊講到黑格爾說的「詞是對物的謀殺」。當我們說出一個詞,比方說當我們說「樹」的時候,也許你想到的是「百年樹人」的樹,也許是你童年回憶的某個印象深刻的一棵樹。我們說到這棵樹的時候,我們指涉的對象物已經是與我們離開的,那保證這個、講的這個樹的意義的大他者已經是不完備。那我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史上大家譽為最有名開頭的小說,開頭開得最好的小說,以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來看,他怎麼開頭呢?馬奎斯寫到說「許多年後,在面對行刑隊的時候,邦迪亞上校便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尋找冰塊的那個下午。」馬奎斯說他寫這句話已經寫了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的構思。從這句話才開始了《百年孤寂》整個六代的故事。邦迪亞上校是這個小說裡面一個主人翁、很靈魂的一個角色,他在某次革命面對行刑隊的時候,他在腦海裡面閃現了過去父親曾經帶他去尋找冰塊。所以在這一句、簡單的一句話裡面,那個冰塊就成了似乎追憶的、無法再現的一個對象。大家如果有看那個小說就會知道說冰塊的命名其實是很有趣的,因為對我們來說冰塊的命名是很可以想像的,我们生活中隨時都可以找的到冰塊,但在小說裡面,因為小說的場景是在馬康多村莊,這是一個熱帶地區,照理說熱帶地區應該不會有冰塊的,所以在小說裡面就是類似像魔術師一樣的長者,叫馬魁迪。馬魁迪他都會為這個主角的爸爸帶來世界各地很珍奇的一些物品,包括說帶來磁鐵、照相機,帶來各種各樣的東西,那其中一次他就帶來冰塊。那邊當地是熱帶,所以冰塊非常的稀奇,所以大家都要去排隊,進入到馬戲團的帳篷裡去看那個冰塊。那大家可以想像從來沒有看過冰塊的人會覺得怎麼樣呢?這是一個真的很神祕、很神奇的東西。那個冰塊他裡面形容很長一段,像玻璃一樣但又不是玻璃、透明的、上面冒著白白的霧氣,當我們觸碰的時候手還會有一種刺痛感。對他們而言,他們沒有感受到冰冷過。書裡面當然就描述成冰塊,當冰塊已經被能指給表徵,進入一個主體的一個能指的系統裡面,那個就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追憶的過去。
我這邊講得比較粗糙,如果就剛剛皮爾士來說,我們並不會認為說,彷彿我們說這個符號時,彷彿我們可以去操作一個對象,或是生產一個意義。拉岡這邊提到一個能指的话,能指的一個說出常常就是對其一個所謂指涉物,或是原物,或是一個對其欲望對象的喪失。我们這邊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形式,这個公式,我们剛剛講的就是一個能指的主体由另一個能指來代表,這是最基本的公式。所以我們舉個例子,讲這個「愛的理由」來說,如果說第一個能指就是一個愛的理由的話,那第二個能指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那我們會問說,為什麼你會去喜歡一個人呢?去回溯的話,齊澤克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我當初跟我的丈夫相遇時,我知道我的丈夫是一個可以叱咜風雲、統攝全局,他是一個在法庭上非常厲害的律師,那時我對他毫無感覺。但是當我第二次我跟他相見時,我知道他連腳踏車都不會騎的時候,我決定給他一個愛的機會,這時候缺陷的理由就變成一個愛的理由。常常這個S1能指我們去追溯起來,這個成為決定我們主體的命運很重要一個起源的S1能指,常常都是回溯起來根本是不成理由的。
那第二個來看的話,我們把這個公式衍伸來看,我們可以說是用一種擴張形式來說的話,一個能指的主體,他除了用一個能指來表徵代表的話,他也可以由其它任何一個能指來代表。我們來看底下的,S1一直傳遞到S2…,我們可以同時說,在集合裡面所有的能指,包含S1、S2、S3、S4…到無窮,所有的能指都可以來代表主體。這時我們會說這群S1能指就是一種能指的蜂群(sworm),這個帶有原初享樂、愛的印記的能指。所以如果可以歸結成底下右邊這個的公式來看,B就是一個專名。比方說我叫俞翔元這個專名,底下S跟兩個標誌(VV)加S就是指主體不能意指自身,所以就是說我意指自身的所有能指,剛好欠缺了我自己這個能指。因此這個專名就只是去縫合、掩飾或是遞補這個缺失了意符自身相關的、所有意符的集合。我們用底下這個大家比較了解,這邊講比較抽象。比方說A集合包括ABCDE這五個元素來說,但是A集合這個名字就會跟底下這個A元素這個是重疊,這就會陷入剛剛所謂的羅素所說的「說謊者的矛盾」,那要避免這樣的矛盾我們會說,那我們就把「A」集合命名成「甲」集合,這個甲集合裏面包括了ABCDE五個元素。簡單來說比如說,我的名字,在這個專名的能指,裡面就是獨缺我這個專名,屬於我自身自指的這個能指。因此拉岡有用另一個例子來看克萊因數群,如果我們要獲得一個完整的能指的集合的話,我們可能就會變成一個互相銜接、頭尾相連的一個集合。比如說我們定義A集合裡面包含了B跟C,B集合包含了A跟C,C集合包含了A跟B,我們就可以避免上述的這種自我自指的,自己包含自身的一個矛盾。那因此畫成圖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底下的三角形,A跟B跟C形成一個三角形,這是一個克萊因數群,或是右邊的四邊形。簡單來說,就是自己所有的能指是有所欠缺的,剛好缺了一個不可命名的那個部分。至於大他者也是不完備的,我們這邊右邊也可以看到,當所有的能指都用來代表變成S1能指,來代表主體的時候,這個S2能指就必不在這個能指的集合裡面,因此S2能指就會變成戈德爾定理的「不完備定理」的一部分。那這個講得可能太抽象,當我們說一個能指的時候,其實是一個主體的消失,我們那個能指並不能代表那個能指的主體自身,它只能連接到另外一個能指。那至於我們那個能指也沒辦法獲得我們的指稱物,我們的物是一個死亡喪失、離開的。
除了說用所有的能指來為另外一個能指來表達主體之外,我們也可以有第三種形式,就是說我們只能用一個能指來代表所有其他能指,這個就像是一個主人能指,比如說芥川龍之介《傻子的一生》裡面有一句話: 「人生就像一本書,它很難稱之為一本書,但它還是一本書。」我們說人生的各種殘缺、各種不完美和各種片段,當他被歸結成人生的能指時,它似乎就全部縫合起來,變成一個集體的、變成一個完整的、有一個人生這個能指去掌握的、去包圍的一個命名。比如說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好了,好像是第八號交響曲是沒有完成的,在他死後大家去集結他的殘稿,把它整理起來把它重新出版,因此這個交響曲被稱作《未完成》交響曲,但是当我們去聽這個交響曲的時候,他裡面殘缺的樂章我們就會無盡地去幫他補充,這樣的未完成在這樣的命名下,就變成一種另外一種形式的完成,他殘餘的部分似乎就会自然地去把它延續、去完成。
或者是你去看一些偉大的人的一些回憶錄或者是筆記好了,比如說現在最被神秘化、最被推崇的維根斯坦,大陸來說是維特根斯坦,我們去看他的筆記好了,他的筆記有一些片段我們看來,單獨看來,你放在網路上的博格或是部落格,或者是臉書、微信上來看,你會覺得其實這根本就是不怎麼樣的句子,比如說他寫說:「為什麼人痛的時候會叫一聲『啊!』呢?」這時候如果說是台南金城武寫的話,我們會覺得這句話根本沒有什麼,可是如果放在一個我們所說主人能指的維根斯坦的名字,他這個《戰時筆記》的名字下面的時候,他每一個這個細微的標點,甚至是這個句段都帶有一种意義在裡面,一種回溯性的意義,我們說這就是S1的能指,他去代表所有其它能指的這個主導優勢的一個特點。
我們講完…再講一個一小段,我們就中間休息一下下。
我們第五個公理就是說所謂能指的介入,它會造成主體的分裂以及主體是認同於一個讀音跟一劃,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們有看過佛洛伊德集體心理學以及自我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當你去探討各種不同的認同的形式,包括男孩的伊底帕斯認同,包括說歇斯底里癔症的認同,包括對原始父親的認同,它歸根到底就是說所有對其他人的認同都可以被歸結成對單一特徵的認同,拉岡會說是「一劃」,這邊講一劃就是講畫筆的一劃,追溯到我們原住民的時候可能還在很原始的階段,我們每次去打獵回來,都會在我們的不管是龜甲、獸骨或者是鼎鑊上,畫下…每捕獲一頭獵物就畫下一道,那就是那個一道、一劃,主體的認同並不是我們單純所謂想像性的自戀鏡像的認同,他最基本的一致性就是來自於這種一劃,象徵性的認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石濤,這個苦瓜和尚曾經說過:「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就是這個一劃。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就是這個一劃,可以看到右邊,我們可以說這邊一劃就是一個「我」跟「非我」或是「主體」跟「大他者」之間空集的那一劃,我們必須要有這一劃,我們才有最低限度的一個象徵性認同的一致性,所以我們這邊,底下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說,這個一劃如果我們去細究的話,我想這個有點太難了,我們就不要講了。
好,這個太難,我們直接跳到公理、命題六好了。那因為這個一劃的話主體才能成為「一」,才能形成「一」,一劃也才能成為我們算數的基礎,所以拉岡說主體是作為一個集合的加一,第一個能指就是所謂的、最具代表性的能指就是墳墓、墓碑、陵墓,我們可以很有趣的發現陵墓、墓碑,它其實是一個像是陽具一樣的能指,同時也是一種活力跟死亡的能指,這樣的「一」就成為之後我們可以數算、可以計數的一個基礎。有個例子:我們說小孩子在數數的時候,可能會說我有三個兄弟,喬治、約翰和我,這時候他把「我」也算進去了,如果皮亞傑的話會說這就代表孩子還存在具體運思期,他的認知思維發展還不成熟,但拉岡不這麼認為,他說這代表我們主體本身就是作為一個加一,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劃,就是表示這個不包含自身的集合裡面加一的部分,因此這個加一就是後來我們能夠數算,進入象徵界的基礎。我原本這邊要講弗雷格的算術哲學,但我覺得這個比較難,看起來好像對大家來講有點太難了,我們就之後再講好了。就是說象徵界的話是零到一,包括自身跟自身相容性、一致性,最低限度的認同,進入象徵界之後我們才有「二」跟「三」,所以精神病的主體可能常常都有數算的困難,就是他沒有辦法進入象徵界,所以他在加一方面就會有他的困難,如果大家之後有興趣,我們還可以細講這個弗雷格的算術哲學的部分。
第七個公理的話我們會說,能指跟能指的結構它有它的先驗性跟超驗性,所以我們每個主體在出生前,我們就被能指的系統、體系、集合給包圍了,所以我們在出生前就有可能被決定了我們的國籍,決定了我們的代際,決定了我們的性別跟輩分,我們在大他者的話語跟欲望中就有了位置,尤其像現在的科技好了,現在的科技已經可以進步到說,我們可以看3D超音波(四維彩超),我們可以在很早的時候就可以辨識孩子的性別,我們可以很早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孩子的影像,所以我們說這個鏡像階段可能比原本拉岡說的更早,現在爸爸媽媽們都可以在婦產科診所,很早就看著電視上的螢幕說:「寶寶這就是你。」跟肚子裡面的胎兒說話,所以我們在出生前,其實就已經被這些能指所包圍了。那第二個的話,能指有這個超驗性,什麼是超驗性呢?能指它的超驗性就是說,當我們的分析者說出一些他經驗所無法經驗的事物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尊重其精神現實,怎麼說呢?他講到說我很害怕,我曾經有個案說我很害怕死掉的山羊,他因為這個關係都不敢出門,而這個時候我就會很奇怪啊!你有看到過死掉的山羊嗎?沒有啊,他這輩子從來沒有看到過死掉的山羊,那為什麼是死掉的山羊?這樣去追溯他能指的話,就一定有它特定的起源,我們說這為什麼?能指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是說,它可以是一種虛構的實體,大家想想看,人類就是這個樣子,人類之所以可以活在這個象徵界中,每天都要去跟銀行,去跟各個組織法人,跟國家、各個單位去打交道,但是這一些都是虛構的,它是由象徵符號的效力去虛構的,但是我們跟它們打交道就像是它們是一個完整的實體一樣,我們說這是一種象徵的、虛構的實體,另外,我們也許在有一些我們認為是邏輯謬誤的事物,比如說方形的圓,或者是金山之類的,但是當我們說出來的時候,按照弗雷格的說法,這個也是一種實體的,不然它是一種想像的非實體,比如說一個分析者他提到說他夢到獨角獸的時候,這個獨角獸也許就是一種想像的非實體,但是這個獨角獸如果去探究的話,還是可以去分析出很多細緻的東西,比如說大家如果去看《幻想與無意識》這個沈志中老師翻譯的,裡面就有一個很精采的分析,一個獨角獸的夢。如果你就只是跟一般的想像的原型或者跟一般的現實經驗的話,他夢到獨角獸就是完全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就精神分析來講,去分析獨角獸就分析出很多有意思的部份。我們可以看到,他從獨角獸(Licorne)這個字本身把它拆分,拆分成Lili跟corne的部份,Lili的話就是作夢的分析者他母親的表姊妹,在夢裡面是一個具有亂倫誘惑的大他者,角的部份,獨角獸頭上的角,還有主人公自己的脚,還有鐮刀傷口的聯想,以及主人公自己對沙子、對皮膚強迫清潔的一個強迫症,延伸到對閹割的恐懼,所以我們說,就算是方的圓、就算是獨角獸、就是金山好了,這些能指也是有必需同等對待之的一個態度。
好,那公理第八個,我們講完…看看講到哪邊來休息一下,我們講到公理九來休息一下下好了。
我們講到公理八,這個公理八算是重點,因此我們總結來說,前面拉岡把能指用函數運算來表達,所以第一個總公式,能指的功能就是把一個能指放到抵制所指的橫槓上,也就是剛剛所講的能指對所指的優先性,所以能指並無法那麼輕易地能達到所指。第二個就是換喻的公式,第三個就是凝縮的公式。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換喻就是能指對能指連結,但是它並沒有跨越跟所指的橫槓。如果就精神分析來說,能指的換喻就是一種欲望的對象的缺失,它代表的是存在的缺失,隱喻的話就是由一個能指替代了另外一個能指,橫越了橫槓產生了意義的效果;如果就分析上的話就是連結到存在的問題跟症狀,這個後面我們可以來講一下。這個換喻跟隱喻,跟佛洛伊德《夢的解析》有所聯繫,跟《夢的解析》裡面的移置跟凝縮結合在一起,拉岡在這個〈無意識字符的動因和佛洛伊德以來的理性〉裡面,舉了隱喻跟換喻的例子,包括換喻的話,他是用「帆」跟「船」之類的關係,因此換喻是一種部份跟整體,容器所容物,或者說時空毗鄰的關係,隱喻則涉及了主體跟能指的替代的關係,因此他舉的是雨果《沉睡的布茲》的例子,他說「布茲的稻穗既不吝嗇也不懷仇恨。」稻穗就替代了布茲,這個前主體的專名就因為能指的替代產生了意義。
如果直接回到臨床來看,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如果說日常的語言的话,我們的精神病理可以看到,遺忘的話就是一種最低限度的換喻,而語誤的話就是一種隱喻,我們來看佛洛伊德舉的例子,這個大家應該都看過,佛洛伊德也是一個拉岡派,佛洛伊德在跟友伴去義大利旅行的時候,他問到他的友伴說:「你有沒有看過辛諾萊利(Signorelli)的一個畫叫做《四個終點》(死亡、夢與想像的天堂和地獄)。他要講這個辛諾萊利的時候他一直記不起來辛諾萊利,他腦中浮現的只有兩個字,一個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一個是波特拉菲奧(Boltraffio),就右邊這兩個字,他一直無法記起左邊原來這兩個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換喻,原本的辛諾萊利換喻到了波提切利和波特拉菲奧上面,當然如果我們去細究的話,之所以記不起辛諾萊利的意思,因為Signor這個音就是義大利文「先生」的意思,那在德文「先生」就是Herr,它跟波希尼亞(Bosinia)跟赫賽哥維納(Herzegovina)這個波赫地區的某段回憶是有相關的,佛洛伊德其實他的內在回想起波赫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土耳其人都是非常敬重醫生的,土耳其人敬重醫生到說,如果醫生跟他說:「你這個病人的病情沒有救了,大概就束手無策了。」當地的土耳其人就會回答他說:「先生,如果你都說沒有救了,一定是沒有辦法了,我們知道,真的是很遺憾。」所以跟先生的Signor跟先生的Herr是有所連結的,另外就是說,佛洛伊德根據死亡又聯想到「性」的部份,土耳其人非常注重性行為,他們如果覺得性功能喪失,就幾乎是比死更痛苦的事情,因此佛洛伊德又聯想到在特拉弗伊(Trafoi),它有一個病人是因為性障礙的問題而自殺死亡,佛洛伊德沒有幫助到他,所以佛洛伊德有所悔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特拉弗伊後面的「弗伊」,跟Herr跟這個波士,波提切利跟波特拉菲奧這個組合,那就造成了一個換喻。雖然說遺忘是一個換喻,但是從左邊來看這個Signor跟Herr它本身也是有隱微的隱喻的成分在裡面。拉岡另外一個有趣的特點講到的是說:「所有的遺忘都是主體自身的遺忘。」為什麼呢?我們知道佛洛伊德叫做Sigmund Freud,西格蒙佛洛伊德,所以他自身對Sigmund也是一個遺忘,所以我們從一般的語言現象就可以看出了這個隱喻跟換喻的層面的一個無意識的運作。
我們看下去,我們看完公理九就稍微休息一下下。
公理九,我們要理解能指的運作的話,我們會注意到能指的共時性跟歷時性,所謂能指的歷時性,就像我講一句話好了,我們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會相互接續,直到我講完最後一個詞的時候,這句話才會完成。所以我們可以說「歷時」是一個水平軸,它是一個語句的合併組合。就前面來說,它也是一種換喻,它是遵守語法句構的一個水平的接續。共時軸就像是一個垂直的線段,比如說我們看左邊這個圖来说,從S到S’ 這個橫向的軸就是所謂的歷時軸,這是一個水平軸,它是由詞跟詞的合併跟換喻組成的,而貫穿這個水平的能指鏈的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共時的軸,這共時的能指環;這個本身的話我們是說,當一個語句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根據最後一個句子去回溯性地去解釋。因此這個垂直的共時軸劃過的地方就是共時的層面,共時的層面我們可以說是一種詞形隱喻或是選擇的軸。如果就剛剛提到的諾曼.雅各布遜來說的話,如果根據水平跟垂直或者說縱向的選擇跟橫向的組合,它可以區分出兩種失語症,第一種是換喻方面的失語症,就是水平軸方面的失語症,另外一種是垂直方面也就是選擇軸、聚合軸方面的失語症,水平軸的失語症是怎麼樣?他的句法是紊亂的,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完成一個很完整的句子,而垂直軸的失語症,他是有一種命名賦予跟同義詞的困難,不管怎麼樣就是說,當我們聽一句能指的話語的時候,它有其水平跟垂直也就是說它有其歷史跟共時的部分,比較詩意的說法,我們可以說能指的共時跟歷時就像一個鏈跟環,它形成一個像網絡或者說一個蛛網密布的一個網子,它包覆住整個能指所謂意涵的世界,但是這樣的包覆是沒有辦法完整的,我們看到右下這個圖,它必定被一個空缺給卡住了,這個空缺就是漁網的塞子,對象小a被閹割的匱缺、空乏的部分,如果就那個鏡像階段來看的話,就好像是中间那個鏡子,大他者鏡子的部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這個共時和歷時的分析,也可以去看羅蘭.巴特的分析,他把这个比喻、比如說交響曲,交響曲旋律的行進就像是歷時軸,其中的和聲配器就像是共時的部分,我們的服裝也是,我們全身的穿搭跟我們某一個衣服的選擇,就像是換喻跟隱喻之間的關係,如果攝影的話,大家去看這個《明室》攝影的雜誌如果大家研究攝影的話一定會看到,所謂展面(Stadium)跟刺點(Punctum)之間的差別,我們看一個照片的時候可以先從整個照片的脈絡去看,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張戰爭的照片,可以看到說畫面上有一個孤苦無依的嬰兒在哭泣,我們看到背後瓦礫堆的廢墟,我們產生一種同理心,我們根據整個照片的展面,羅蘭.巴特會說是展面,羅蘭.巴特說這樣的展面是基於教育性質的體悟或者理智的理解,但是會刺痛他的隱喻的點,他叫刺點,那個刺點是一些很細微的細節,也許是畫面模糊的一個點,或者是一個無關的細節,那個卻是隱喻閃爍的地方。
我想中間這邊我先休息一下下好了,因為接下來講的應該是重點,今天講的重點,包括所謂的隱喻、父之名、父性隱喻的介入,這個跟我們的精神結構,所謂我們伊底帕斯的三個時刻,有重要的相關,我們之所以隱喻的話,必須要有一個錨定點,這個需要父之名的介入,因此有了理解臨床上三個結構的區分,最後我們再講述一下,很快帶過佛洛伊德的四個個案,包括小漢斯、狼人跟鼠人還有史瑞伯這四個個案,我們很快速地帶過,我們這邊先休息,休息個五分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