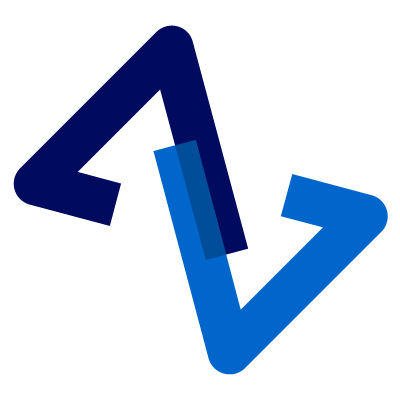俞醫師金句摘錄
我要、要什麼是必需經過這個大他者的編碼的位置,來獲得一個資訊知道我們欲望的對象是什麼。那這個大他者,拉岡這邊所謂的大他者就是前面講的能指的寶庫、庫藏,它是一個編碼處,一個知識的場域、真理的場所。
我們欲望是由大他者欲望所去構建的。所以拉岡說主體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那這個大他者的欲望呢,的欲望就法文來講其實有一種含糊的意思,它可以是英文的of也可以是英文的for, 所以它既是對大他者欲望的欲望,也是慾望成為大他者所欲望的。
當我們進入了現實原則的時候,我們尋找的永遠是一個根據理解判斷下的一個替代物。而當初的那一個永遠失去不可能的,就是經過再現性思維不可獲得這個原物das Ding,這個後續所謂das Ding就是在實在界的部分。
原初照料者跟第三方,第三方的禁令,把這個原初失落的這個實在變成不可能,因此這個第三方的禁令,不允許就取代了不可能。
原自戀就是永遠的認同這個已經喪失、失落、離開的原物,這就是das Ding的原物,我們說抑鬱症就是這樣子,他藉由抑鬱來避免哀悼,他永遠的認同了那失落的原物。他藉由擁有認同於失落的原物他就永遠不必再去失落了。
次級自戀的話我們說是其他的主體,比如說認同於想像性的陽具,還沒有辦法放棄自己想像性的陽具。
當主體跟原初照料者相互融合的時候,其實他會感覺到這原初照料者的全能,本身是一種很無能的焦慮狀態。他充當著母親想像性的陽具,這種焦慮更拔高擢升。這時候他會呼求一個分離。因此如果佛洛伊德是說分離的焦慮,拉岡會說是無法分離的焦慮或是欠缺的欠缺才會有的焦慮。
如果在第一階段父親的禁制、父親禁止母親的享樂,原初照料者把孩子作為享樂,或是對母親的享樂。這時候的失敗就會變成父之名的排除,這是一種除權棄絶或是對岸叫做排除,那這時候就是一個精神病的主體的結構。
如果從第三個階段退行到第二個階段,就是說他進入閹割、卻拒絶閹割,那倒退回來,那是倒錯,他就是沒有辦法放棄、不能接受父親對母親的閹割。
那經過這樣的閹割的話我們才可以從φ(小phi)變成Φ(大phi),就是所謂的陽具的能指。所以這個父之名、父性的功能、父性的隱喻才能夠讓我們剛剛不盡滑脫的能指有一個錨定、縫合或是黏扣,我們才有一個隱喻,我們話語才有可以解讀的最低限度的意義。
母親實在乳房和母親本身作為一個亂倫享樂的禁制,是永遠失去das ding這個原物的存在。這個實在界我們是永遠無法獲得的,因此是一個極需要去迴避,他去太過於接近反而會變成一個可怕或驚怖。
前面的欲望和現實的邊界,快樂原則其實是屏擋,是作為一個善去屏擋我們去接近實在那個幻想,而美是最後一道屏障。
伊底帕斯的三個時刻就分別對應到我們三個精神結構,包括精神病、倒錯跟神經症。他們之間經歷過有三個不同的問題;要不要成為陽具?要不要接受閹割?最後接受閹割,我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還是兩者兼有。分別形成不同的機制,包括排除、拒認跟壓抑。
好像我們看到精神病的話,他的能指世界是詞等於物。那倒錯的話是詞和物相互游離,那神經症的話是物的喪失和詞的滑動。
如果就布魯斯.芬克來說的話,精神病的邏輯是什麼?就是既不這個也不那個。倒錯的話是既這個也那個。神經症的話是可能是這個或者是那個。這是不同邏輯。
精神病的人、精神病的主體是無法做夢,他的生活就是一場噩夢,所以他沒有辦法醒來。對他而言的話,這個夢跟現實是無法區辨的。
神經症的話,他來到分析,就是說它從他的原本的無意識的夢中驚醒,他沒有辦法繼續他的精神工作。它的症狀就是一個待解的謎,所以我們要把它接續他繼續的夢。
倒錯它等於說是像法西斯極權主義一樣,它是一個美學政治化或是政治的美學化,他的生活就是遊戲,他的遊戲就是生活。
我們可以說完備的集合就是所謂男性的集合。也就是所有的集合,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陽具能指或者要接受閹割。但是這個裡面其實蘊含著至少有一位像原父一樣的人物,他是不受閹割的,它蘊含的這個例外,是一個具體的例外。
性關係不存在有很多種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說兩性的話必定有大他者介入,
必定是有大他者介入,沒有直接兩性相對相稱。第二個是大他者能指體系之中只有陽具能指,沒有其它陰性的能指。這個陽具能指本身也是欠缺的能指。第三個的話,女性是非全的邏輯,沒有一個定冠詞全稱的女性,她只有個別的女性。
臨床的話能指跟症狀關係是什麼?症狀是作為能指的函數運算,拉岡有一個公式就是症狀sigma(西格瑪)就是一個F函數帶入S1能指,所以症狀是作為一個能指效果的存在。
小漢斯的部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症狀本身其實也可以作為一種隱喻或凝縮。就是這個畏懼症本身就是一個象徵閹割或父親介入的想像性的替代。
症狀除了是作為能指作為大他者那邊來的訊息,作為一個凝縮或者隱喻,那麼最後拉岡的中後期也把症狀視為一個無法分析的聖狀,跟享樂的海岸線相連。
精神分析的重點並非是意象或是我們想像中的轉移,我們還是要回歸到最根本的對能指的注重上,對這個能指本身的細讀來說的話我們可以獲得很多。
拉岡精神分析的本身是非常的深奧,因為拉岡本身不管是借助了人類學、語言學、邏輯學、拓樸學想辧法去描繪或是接近精神分析者的無意識,但聽不懂的話可能代表分析者本身比你想的還要難以理解。當我們可以在想像中藉由簡單的轉移、反轉移就可以去掌握的話,那人就太簡單了。
我們常常說認識論本身的困難就是本體論本身的困難,我們使用工具的缺陷就是可能就是我們認識本身對象的缺陷。所以拉岡學問本身的困難正反映了我們覺得臨床本身的困難。
我們不會那麼簡單地去化約或概括一個精神分析的分析者的個案陳述。我們可能必須都要從能指出發,比如我講的這個,包括小漢斯很畏懼症怕馬的這個馬本身,我們也可以去解析去分解它本身的音素。它的本身的凝縮或它滑移的跟語言的關係。
拉岡派的精神分析的特色就是它每一次的會談是一個彈性的時間,它並沒有說一次是45分鐘還是50分鐘,它是彈性的時間,因為無意識的邏輯時間並不是一般鐘錶的時間。
精神分析的長程到底一般是多久,這就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根據每個無意識主體他的各自獨特性,單殊(singularity)、個別性去決定的。也許跟每個人頓悟的時間不一樣,每一次都是一個小次的閹割。完整的閹割每個人需要的次數都不一樣。
你自己從分析中得到的理解也許會比聽課或是看書來得快,通常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你自己也會燃起對自己無意識的欲望,而對無意識的欲望拉岡會說是一個比死或是比強迫重複,重複自動性更強的一個力量。
對無意識的欲望是可以去推動去,不管是做分析、成為分析家也好、或者說去閱讀也好、去更好的言說也好,因為拉岡後期很講究這個善言,好好的說,學理論是為了更好的分析自己。
笛卡爾講我思故我在,那麼拉岡會說這個我思故我在是錯的,中間的故是一個空集,他會說或我不思或我不在,我要嘛我在,要嘛我思,我不能兼得。當我在的時候是它在而且我不思,當我思的時候是它思而我不在。
精神病我們會說他的機制是所謂父之名的排除,父之名的排除大家可以看到最簡單來說就是他沒有辦法形成一個隱喻,雖然他的所指跟能指會不住的滑動,所以他沒有辦法有一個錨定點,所以最簡單地說他是沒有辦法懂得隱喻的。
精神分裂症的話,他這些妄想的系統其實也是形成一個妄想性的隱喻來穩定自己,所以妄想的形成也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所以我們會說是一種Delusional metaphor,妄想性的隱喻,所以分析家要去協助這個精神病去組織其妄想,讓他的妄想可以穩定其自身然後遠離身邊的人,不要造成他生活的影響。
神經症的話還可以經過異化跟分離,還可以跟對象小a分離,還可以放棄這個作為想像的陽具,才可以穿越核心的幻想,去追尋自己的關鍵的能指而去言說,認同自己無法去除的症狀。
精神病沒有進入到分離。精神病我們只能做到包括對他的享樂的限縮,還有包括想像性的支持,以及他象徵的這個增補,讓他藉由聖狀或是藉由妄想的隱喻的建立讓他可以穩定下來,那他也可以好好的生活,甚至利用他的聖狀去追尋有意義的人生。